
圖:四枚篆刻印稿:“嶺南客”(李賀忠刻,左上)���,“寄荃齋”(陳浩刻�����,右上)����,“青鳥賦”(鄭朝陽(yáng)刻����,左下),“胡不歸”(李澤潤(rùn)刻�,右下)。
我自幼喜歡印章���,這么說并非空口無(wú)憑��,有兩件“物證”留存至今:一件是少年時(shí)寫的一張“書法”���,被母親小心翼翼地保存下來���,直到母親去世后,我才重新看到��,驚奇地發(fā)現(xiàn)那上面竟然鈐著一方名章�。我一眼就認(rèn)出,那是我上小學(xué)時(shí)用肥皂刻的──那肥皂早已杳無(wú)蹤影�,但彼時(shí)的“處女刻”竟還留下了印痕,何其難得也���;另一件是一塊黃色長(zhǎng)條狀石頭��,上面有“侯軍”二字的淺淺刻痕���,那是我的第一方自刻印章。我從未擁有過專業(yè)刻刀�,這石章八成是我用鉛筆刀刻的,故而刀痕很淺�����,但線條還算爽利。這件“作品”我一直保存著���,至今還珍藏在我的印盒里���,石頭的包漿已經(jīng)很厚了。
有這兩件東西作證����,足見我與印章還是很有“前緣”的?����?上?��,有緣未必成“眷屬”,只因后來移情別戀��,迷上了書法���;拜入師門后�����,書法老師并不治?��?;此后����,十八歲就進(jìn)報(bào)館當(dāng)記者,整天忙得昏天黑地�,別說治印了,連書法也顧不上了�����。就這樣����,蹉跎歲月幾十年,我再也沒碰過刻刀����。
不過,對(duì)篆刻藝術(shù)的愛好卻是刻進(jìn)骨子里的。有道是“有緣千里來相會(huì)”�,誰(shuí)能料到,我在年近花甲時(shí)��,卻如靈光乍現(xiàn)���,竟然鼓搗出一個(gè)“集印為詩(shī)”的新玩藝兒──以閒章的詞句為基本語(yǔ)言單位�,重新排列組合����,抒發(fā)自己當(dāng)下的情感和意念,幻化為一首首新詩(shī)�����。這么說不好理解���,且舉例說明:集印詩(shī)“獨(dú)處忘言臥看山�����,青山問我?guī)讜r(shí)閒?長(zhǎng)與東風(fēng)約今日�,不捨春風(fēng)又一年。”這是我在臨退休時(shí)寫的�����,表達(dá)的是希望早點(diǎn)放歸江湖的期許之情����。這首小詩(shī)用了六方印章,分別是“獨(dú)處”�����、“忘言臥看山”����、“青山問我?guī)讜r(shí)閒”、“長(zhǎng)與東風(fēng)約今日”��、“不捨”和“春風(fēng)又一年”���。所謂“集印詩(shī)”�,就是這么連綴演繹出來的����。這些印文是從千百方印文中精挑細(xì)選����,比對(duì)錘煉��,組合成詩(shī)的����。而這些印文,有些是出自我的印章收藏�,有些是得自藝術(shù)界朋友的自用閒章,有些則是征得印章收藏家的慨允����,我去打來的印蛻……總之,每一枚皆來之不易���。集印愈多��,詞匯愈多���,制作集印詩(shī)詞的空間就愈大,作品也就愈加豐富多彩……
這樣的新玩法�����,我孜孜矻矻作了十年���,作出的集印詩(shī)詞少說也有一兩百首了���。以這些作品為“母本”,深圳的兩位篆刻家陳浩和李賀忠還與我聯(lián)袂���,先是于二○一三至二○一四年舉辦了“集印為詩(shī)”巡回展(深圳��、汕頭����、包頭��、天津�、海寧);十年之后的二○二四年又舉辦了一次“集印十年”紀(jì)念巡回展(深圳�、德化、上饒�、嘉興、海寧)……
這一路走南闖北����,逶迤而行����,所到之處�,我竟然時(shí)常被不明真相的朋友們稱為“篆刻家”了。我起初還忙著解釋“我不是篆刻家�,只是喜歡篆刻……”但,似乎并無(wú)效用����。在人們的印象中,你都發(fā)明了“集印詩(shī)”�,還搞了這么多展覽,怎么可能不會(huì)篆刻呢�����?遇到這種情況��,我只能聽之任之了�����。
其實(shí)���,在中國(guó)傳統(tǒng)文化中���,早就有一個(gè)約定俗成的說法����,叫做“善書者不鑒�����,善鑒者不書”�。清代袁穀芳曾直言:“天下有不習(xí)其事�,而能言其義者乎?有之矣����。卞和以識(shí)玉名,非以能雕琢玉名也��;伯樂以識(shí)馬名�,非以善馭名也。知畫者不必工于畫���,知詩(shī)文者不必工于詩(shī)文����。理之所通,以意悟之而已��?!保ㄒ浴吨袊?guó)印論匯編》第八百六十一頁(yè))這段話說得明明白白──善畫并非鑒賞繪畫之前提,善詩(shī)文也并非進(jìn)行詩(shī)文品鑒的必備條件�����,關(guān)鍵只在于“意悟”二字��。一個(gè)人懂得“意悟”且善于“意悟”�,就能做到“理之所通”:以理鑒畫,以理品書���,以理賞印�,那你就是書畫印評(píng)鑒領(lǐng)域的卞和與伯樂����。置諸現(xiàn)代,你就足以當(dāng)?shù)闷稹八囆g(shù)評(píng)論家”的稱謂了����。
由此看來,藝術(shù)創(chuàng)作與藝術(shù)鑒賞本是兩片水域,雖說互相交叉��,渠聯(lián)溝通����,但其實(shí)是兩種學(xué)問?�?墒墙倌陙?��,隨著西風(fēng)東漸古風(fēng)式微,這種傳統(tǒng)分工也逐漸淡化乃至消弭了����。尤其鑒賞一門,好像越來越?jīng)]有獨(dú)立性���。時(shí)常聽到這樣的質(zhì)疑之聲:你都不會(huì)書法����,還能批評(píng)書法的優(yōu)劣��?你不會(huì)畫畫��,就不要亂指摘人家的畫作……言之鑿鑿����,似是而非���。殊不知,鑒賞與評(píng)論原本就是一項(xiàng)獨(dú)立于藝術(shù)創(chuàng)作外的學(xué)科�。篆刻家與鑒賞家,互相依存���,互為表里── 就如同我并不操刀治印���,卻完全可以鑒別印章的高低優(yōu)劣,欣賞篆刻的美丑妍媸����。當(dāng)然,精于鑒別和欣賞尚屬鑒賞家的本業(yè)�����,倘若這個(gè)鑒賞家還喜歡寫詩(shī)�����,賞著賞著,驀然發(fā)現(xiàn)了印章中蘊(yùn)涵的濃濃“詩(shī)意”���,一步邁進(jìn)這個(gè)宏大淵深的文學(xué)寶庫(kù)���,那就來玩“集印為詩(shī)”吧──以我個(gè)人的沉浸式體驗(yàn)而言,我與篆刻其實(shí)就是這樣一個(gè)從喜歡到欣賞�,從欣賞到收藏,從收藏到發(fā)現(xiàn)���,直至以“集印為詩(shī)”這種自創(chuàng)的藝術(shù)形式�����,打開印章中貯藏的文學(xué)寶藏的奇妙旅程。
篆刻從遠(yuǎn)古走來�����,原本只是身份憑證���,諸如皇帝璽印���、各類官印乃至名章齋號(hào)等等。宋元以后,尤其是明清兩代����,軟石被發(fā)現(xiàn),使得文人們開始以刀為筆��,揮灑治石���,各騁才思�,抒情言志�,三言兩語(yǔ),意蘊(yùn)雋永����,遂使閒章風(fēng)行于世,絕妙好詞層出不窮��。然而���,從古至今�,除實(shí)用功能和藝術(shù)鑒賞功能之外����,蘊(yùn)藏在閒章中的寶貴的文學(xué)資源�����,似乎一直未能得到深度開發(fā)和有效弘揚(yáng)����。無(wú)論印家還是藏家�����,大都只專注于刀法技法方寸之美����,對(duì)篆刻的文學(xué)價(jià)值普遍認(rèn)識(shí)不足,這豈不是太可惜了��?故而�,我在此倡言:珍視印章中的那一縷“詩(shī)意”����。
作者簡(jiǎn)介:侯軍,藝術(shù)評(píng)論家���。已出版各類專著二十馀部����,包括文學(xué)作品《青鳥賦》、《收藏記憶》���、《雪霽》�����、《那些小人物》����;藝術(shù)評(píng)論《東方既白》���、《讀畫隨筆》�����、作家研究專著《報(bào)人孫犁》以及藝術(shù)家傳記散文集《孤獨(dú)的大師》�、序跋集《守住寧?kù)o》等����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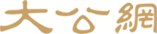


 京公網(wǎng)安備11010502037337號(hào)
京公網(wǎng)安備11010502037337號(hào)